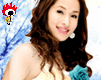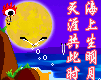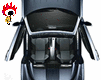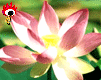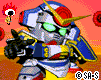| 黄蓓佳:没有名字的身体(14)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9/20 14:55 当代 | |
|
作者:黄蓓佳 医学书上对“宫外孕”的解释是这样的:孕卵不在子宫腔以内,而在宫腔以外种植和发育。其中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多见,约占98%。患者早期与正常妊娠没有明显区别,但随着胚胎长大,可以穿破输卵管壁或自输卵管伞端向腹腔流产,造成腹腔内出血,甚至因失血性休克威胁孕妇的生命。 我们学校所有的人,全体师生,都知道了“宫外孕”这个神秘的词。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性教育就是这样启蒙的,来自于日常,从我们周围的生活中耳濡目染,加上我们自己的揣度、想像、心领神会和触类旁通。 宫外孕。我们在心里默念这个词。我们想像着子宫是什么样子,受精后的卵子又是什么样子,以及受精卵为什么不肯安分守己地在子宫内做巢,而要跑到另外的什么地方捣乱。我们浮想联翩,心跳加快,目光灼亮,以为自己已经分享了成年人的秘密,从此生命就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某种程度上,对性的想像是一种本能和天赋,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体,需要得到人类如何生存繁衍的最权威的解释。 他和他的妻子,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启蒙者。有一点荒诞,也有一点偶然。 不幸的事是,在那一次的外科手术中,他妻子被切除了子宫。他们两个人都还年轻,二十多岁。 袁小圆又到我家里来了。 是在夏天的晚上,父亲母亲都在医院里值班。他们经常要值夜班,用一把铁锁把我们三个人反锁在家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他们不锁门,由我们在临睡前从里面把门销插上的话,他们回来时就很难把门敲开,因为我们一个比一个睡得更死,常常是邻居被叫醒了,我们还没有醒,邻居们很有意见。 其实锁门也就是一种形式,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我们住的是平房,朝南一排玻璃窗,夏天窗户都是开着的,手扒着窗沿,身子一耸,轻而易举就跃上来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连我妹妹这样瘦小的人儿,都能够出出进进如入平地。我们很喜欢从窗户里跳进跳出的游戏,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出门的理由,就把铅笔橡皮扔出去,再翻窗出门捡回来。那个时代的少年们就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平淡的生活过出不平淡的滋味。 袁小圆很规矩,也很客气,他绝对不会在黑暗中冷不丁地蹿上我们家的窗台,然后贼一样地跳进屋里。他来了,就在外面轻轻敲击某一扇窗户,“嗒嗒嗒”三声,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像战争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我哥哥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眼睛发亮,喜形于色,豹子一样敏捷地跳起来,奔到窗口,伸出一只手去。袁小圆在外面搭住他的手,脚底下一用劲,长腿就迈上来了。他从来不像我和妹妹那样,要把肚皮贴在窗沿往上爬,他嫌那样的姿态不雅,还会弄脏他雪白的衬衫。 袁小圆带来了一盒棋,他要跟我哥哥下象棋。他把土黄色卡其布的西装短裤束在衬衫外面,短裤上系的是一条军用皮带,半旧,有一种不动声色的高贵和威严。我想这皮带肯定是他爸爸送他的,我哥哥说过,袁小圆的爸爸是团职干部,在上海驻军。那天他还穿了一双咖啡色塑料凉鞋,跟他的短裤及皮带的颜色十分般配,所以我印象深刻。 袁小圆一来,我哥哥就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里屋我父母的房间里去了。当时我和妹妹在外屋饭桌上合看一本小人书,打仗的。我对写打仗的书一向有兴趣,我妹妹却不喜欢,一看到死人断腿的场面就要捂眼睛。她老是催我翻页。我们头顶上吊着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灯光昏黄,时不时有米粒大小的蠓虫从窗外飞进来,绕着灯泡飞舞。虫子的身体绿得很漂亮,翅膀掀开是一层层的,轻纱叠起样的。虫子不咬人,但是飞翔中冷不丁地撞到我们的脸上,皮肤就有微微的蜇刺感。 袁小圆一来,我的心思不在小人书上了,我的眼睛继续瞄着书页,耳朵却弹簧一样不断地伸长,一直伸进我父母的房间,听那里两个男孩子的动静。我希望能听到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他们下棋时会不会争吵,袁小圆是不是比我的哥哥更加聪明,肯不肯在棋盘上痛下杀手,把我哥哥弄个人仰马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传奇玄秘 > 《当代》小说精华选读 > 正文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