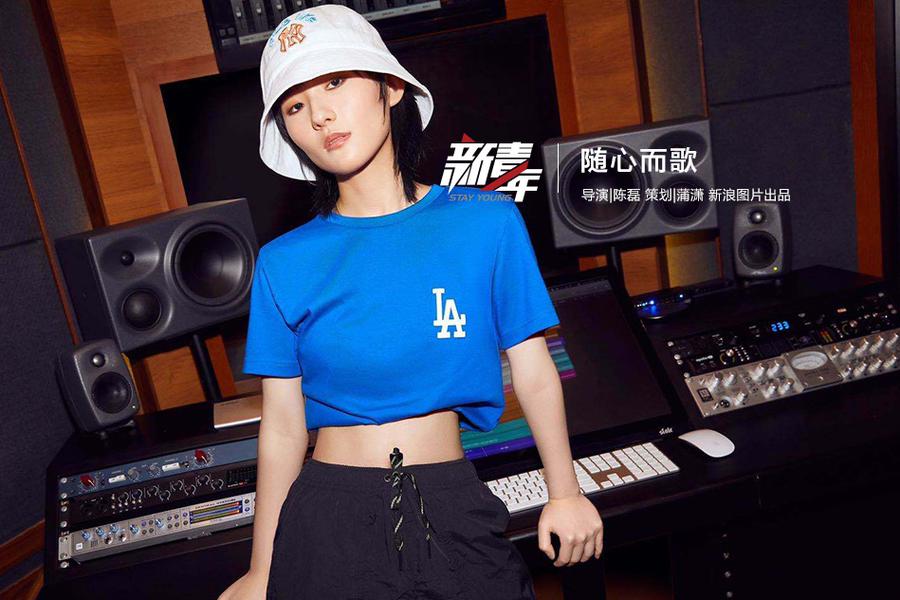张力奋新书《牛津笔记》立体书影
张力奋新书《牛津笔记》立体书影启发俱乐部第10期 |罗振宇与张力奋对谈《牛津笔记》
时间:2020年9月2日20:00
嘉宾: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FT中文网荣誉创刊总编辑
主持:罗振宇 得到app创始人、资深媒体人
以下是本次活动的文字实录:
《牛津笔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其实在它的背后,我更希望说的是一个一直困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解决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如何记录和保持我们的记忆。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我在1988年离开上海复旦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在2017年在牛津的70天的时间里能够把这个世界的感受装到《牛津笔记》当中。三年前,我做了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我自己个人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我把从伦敦家里的75箱书,从伦敦运回了复旦,我记得当运到复旦的时候,搬运工人跟我说,张老师你这些书加起来差不多有2.7吨。我觉得这对我的个人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件。但是到了老罗现在讲的电子书时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一个光盘可以储存50亿的字节,每个光盘至少可以储存5000本书,我们从印刷文明的附近,现在到数字文明的附近,其实我们有了一个极大的跨越,这个跨越对我们人作为一种生存,作为一种存在,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说的一件事情。
中国可考的历史有5000多年,在座的很多人对英国有兴趣,英国可考的历史最多不超过1500年,在中国面前,它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谈到英国,我们觉得它像古希腊,像古罗马,像一个古国,这是因为它对历史的态度,在这本书当中,我想看一看一个古老的中国如何来看待另外一个相对年轻,但是又给你一种非常古老的这样的一种怀念的文化,它到底是什么。老罗说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书,老罗没这样说,我自己这样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四不像的书,至少在文学上非常难以界定,我说它是一本混血书,在读本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知道有一位中国的华裔作者叫蒋怡,在座的朋友知道他的人,读过他的书的,举个手,这个就叫蒋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生于江西九江,曾经参加过北伐,学的是化学,后来到英国留学,他成为英语世界当中被认为是旅行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到了英国以后,几乎从来不用他的母语写作,他总共写了超过20本对世界上重要的城市的,每一个城市他写一本书,从伦敦到爱丁堡,到牛劲,到波士顿,到纽约,写过很多很多的城市,但我每次看他的书,我觉得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从来没有忘记老罗刚才所讲的附近,他永远的把附近作为他人生和感情体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参照。其实在我留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蒋怡的存在,他离开中国九江的时候刚刚过了20岁,当他在70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70多岁,整整离开半个世纪,但是他依然能够讲一口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九江话,能够画非常有中国风格的画,还有他的字。所以,即便他在50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用母语写作,但是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为他说中国话、画中国画,能够写一笔非常非常好的中国字。
下面我们想看看,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古文明和另外一个相对年轻的文明接触的时候,在牛津的这样一个空间,大家都知道钱钟书,这是我这次花了不少时间说服钱钟书的母校,也就是牛津大学学院叫艾克赛特学院,他们告诉我说,有关钱钟书的文字和档案资料,目前存档的还有25件,但是大部分从不公开,因为这是属于他个人的,当时我就跟艾克赛特图书馆的馆长说,能不能拿出一件来,最后他们拿出了这一件。这是钱钟书先生1930年到牛劲报到以后,他的副院长对他面试的一个记录,其中最有意思的,他讲了两件事情,钱钟书先生跟他的副院长说,我的姓钱,跟法语的狗发音非常接近,拜托拜托,在学院里面你们一定换一个发音,否则我每天会闹成大笑话,这里面他特地说到这个事情。另外,他说到刚到牛津的第一天就摔掉了半颗门牙。所以,短短的这样一张卡片,记录了他的生日,他的父亲钱基博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他的导师是谁,他需要关照,看到没有,法语里面就是狗,他不希望还没有入校,已经有了一个有关狗的绰号。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一个中国人来到牛津的时候,他和当时的文化之间所出现的一种碰撞,最有意思的是,这些资料还都保留下来了,这是我在过去三年当中回到母校复旦以后,花了不少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力重建学校的档案,重建学院的档案,当我看到钱钟书先生当年在牛津短短的三年时间,还保留下如此完整的有关他的学习档案时,我们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我们如何来保持记忆,如何来记录记忆。
牛津之所以出名,今天在座的有一位是我在牛津访学期间的我的年轻朋友叫何流,我在书里多次提到他,他现在就坐在下面,他现在在舒什明学院继续深造。大家都知道,牛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Oxford Union,不是牛津的学生会,指的是牛津的辩论社,在座的朋友有没有参加过牛津的辩论社,目前为止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辩论社,几乎每个晚上都有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公众人物在那里演讲,或者学生在就一些大的问题,大的世界的问题,宏大的叙事的问题,在做辩论。我记得我看到过一本书当中,在希特勒决定向欧洲开战之前,牛津辩论社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非常出名的辩论,就是说一旦纳粹对英国开战,英国学生应该是持有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当时令丘吉尔感到非常非常暴怒的一件事情,当时牛津的学生,就是坐在底下的学生,以大多数的反对票否决了这个提议,说如果开战的话,我们将决定不站在政府的一边,我们将不支持对德国宣战。但是实际上的一个情况,下面我想专门讲一本书,这本书叫《OXFORD UNIVERSIDY ROLL OF SERVICE》,我现在收藏的一本比这个更加古老一些,大家能猜一猜这本书是讲什么的。这本书总共693页,很厚,我这本书是500多页,这本书是从头到尾记录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牛津大学的学生最后奔赴战场的所有人的资料,每个人会有两行,某某,生日,哪个学院,什么时间参军,奔赴哪个战场,是否受过伤,是否最后阵亡,如果阵亡的话,他埋葬在哪里,整个一本书完完全全记录了牛津师生对一战的贡献。我特别注意到当时的这个编辑,特别提到他们是花了多长时间编撰的这本书。
我今天主要想讲三个观点,老罗说,我一般不太下结论,可能部分是因为我的职业的习惯,因为作为一个记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如何来描述事实,然后我的读者可以自由的对我陈述的事实做出判断,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观点。第一个问题,刚才提到记忆的问题,其实我们个人的记忆,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个人的记忆是极不可靠的,为了这本书,我大概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希望能够核实我在这个书当中,我要检验一下我的记忆是否确实,幸好我还保存了30多年前的一些日记,或者说类似日记的一些记忆,我才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文字材料的存在,我会断然地否认有些事情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的记忆是极不可靠的。如果我们的记忆很不可靠,我们的文明如何来保存记忆,我们又将保存记忆的职责将给谁?比如这本书在开印前两天,非常幸运,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纳粹上台以后,德国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学家,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他是个犹太人,他非常早的就闻出了味道,最后决定流亡美国。还有两个重要物理学家,都是研究量子物理的,一个叫海森堡,还有一个叫普朗克,我当时发现这两位在国际地位相同的物理学家,但一个是反纳粹的,一个是拥护纳粹的,但我的记忆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错误,我把两个人对纳粹的态度完全换了一个个儿,所以我说,我们对我们的记忆不要有过度的自信。
但是记忆,特别是个人的记忆,老罗刚才对我的这本书有些解读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特别是在我的序当中,我特别想说的是我是一个不相信宏大叙事的人,我宁肯相信碎片化的记忆,碎片化的记忆,毕竟对我们最后还原真相、还原我们的记忆提供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宏大的叙事是记忆之墓。那么,历史、记忆为什么重要,尤其对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古文明传统的国家,一方面我们有古文明,同时大家是否有这个感觉,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短记忆的社会,我们的记忆越来越短,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朋友,几乎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讨论什么话题,为什么?是因为技术,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还是其他更加深层的一些文化的原因,是不是我们选择忘却,选择忘却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种更好的保护呢?《牛津笔记》当中的一句话,我希望能够启发大家,或者启发自己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记忆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对一个个人所具备的意义。
我有一个英国的记者同事,大家对苏格兰公投还有印象吗,苏格兰公投的时候我在爱丁堡报到,我跟一位很多年没有见面的英国同事碰到了,他的家就在爱丁堡,他居然选择在公投的那年学术假,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掉轨的事情,我说你在干吗,他说我刚买了一个三百多年的老屋,所以我请了半年的假写一本书,是给自己看的,不出版,就是把这栋房子的历史搞清楚,为什么这栋房子的历史对他作为一个个人和个体那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
第二个问题就是记忆是要靠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下面那张照片在我的书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这是我在牛津客座的学院叫新学院,其实语言是非常误导的,1379年的一个学院,但是叫新学院。河流的学院稍微年轻一点,河流的学院是十九世纪的学院。这个牛津餐厅的栋梁之谜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牛津和剑桥学院建制中一定要有类似于哈利波托小说里那么大的有魔力的餐厅,这就是新学院的餐厅。故事是这样说的,在二十世纪初就在这个餐厅,每两年每个学院都会请专门查木头有没有蛀虫的职业,发现整个横梁,直径2米长度45米的梁已经蛀空了,当时他们遍查了所有地方,他们都无法找到能够更换这个梁的新的柱子,当时有一个院士就说我们在英国各地有那么多的地产,说不定哪块森林里面真的种了哪些树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木头来换,后来果然他们在距离牛津300多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管家,管家说我们已经等了很多代,每一次管家退休的时候都会留下一句话说那片森林里面的那些木头是专门为这个餐厅有朝一日换木头的,所以记忆是这样保持下来的。
还有一个照片我想特别说一说,刚才我提到了,记忆到底靠什么样的语言。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过读书的时候自以为我用的语言是比较干净的,我很少用形容词,我也很少用成语,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成语在经过无数次的革命和政治之后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当时语义上的功能。但是我到了英国读书以后发现其实我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对我的母语的反省,而这位老先生就是我在校外的一个英语老师,我当时小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所以我当时面临我的博士论文处在一个完全无法完成的心理的恐慌当中,我称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英语殖民主义者,他的严酷他的严格,我跟随他学英文整整三年时间,每星期四一个下午。我从他对语言,大家知道英语是杂交的语言,它来自于各种语言,但是它为何最后成为一个语言的大国、一个文学的大国,我从他们身上我从英语身上对自己的母语做了很多反省,大家如果读我的这本书的话,希望有一些有意思的思考。
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刚才说我们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个体的记忆国家的记忆需要一种好的语言、一种干净的语言、一种能够思辨的语言来完成,这张照片沿袭了英国舰队街,英国新闻报业都集中在伦敦市中心的某一条街,很短不到200米长,所有报纸都集中在那里,那里有个传统,当一个同事退休或者离职的时候,当他完成最后一天工作的时候,他的同行他的同仁如何来表示对他一生工作的尊敬。我当时在英国伦敦工作的时候,有时候突然之间会听到我们办公桌上有人轻轻的敲桌子声音,然后你就听到从这张桌子到另外一张桌子,跟老罗你们得到的办公室一样大的上百人的同事最后都参加到了桌子的敲击声,为什么他们无法起立去送这个同事,是因为往往在5点到6点的时候正是报纸的截稿期,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他们的座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告别这个同事。
这是告别仪式上的另外一个小小的礼物,比如当我辞职的消息宣布以后,我的同事就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完全在秘密的情况下收集了所有有关我的八卦,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买过名牌,他们把我的头切下来以后放在了这个西装上,这张照片是采访温家宝总理,这是真的,但是除了这张照片以外的所有其他内容都是跟FT平时做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的,里面全部都是假新闻,我故意用了一个不是特别清晰的版本给你们,因为我不希望你们看到有些内容来破坏你们对我的美好印象。
总结一下,语言对我们保持记忆、语言对我们记录记忆,尤其中国现在成为一个新的生存状态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母语过于模糊,我们的母语非常难和其他文化有沟通,我们的语言需要一种复兴。我记得20多年前我正好去哈佛做一个节目,去看望了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她是哈佛历史上的第一个华语教授,她是个音乐学家。我在这本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一种情绪,其实我对我们这代人是很悲观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很失望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过于民粹、过于狭隘,所以我当时就表达了对她的父辈也就是赵元任胡适先生的崇敬之情,他们到美国留学参加的第一个组织叫全球公民俱乐部,我希望我们这代人对这个世界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母语的遗产,也能够同样有这样一种包容的心情。

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更多精彩内容随你看。(官方微博:新浪新闻)
推荐新闻
- 【 新闻 】 TikTok美国业务不卖给美企?外交部回应
- 【 军事 】 舰载预警机是怎么发展成今天这副模样...
- 【 财经 】 纽约年轻CEO被分尸 现场还有插电的电...
- 【 体育 】 美网蒂姆5盘逆转兹维列夫 首夺大满贯...
- 【 娱乐 】 老公曝光?神秘男带万茜女儿与妈妈团...
- 【 科技 】 鸿蒙手机终于要来了 华为能否绝地求生...
- 【 教育 】 民办重点高中违规开办复读班近十年 教...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4000520066
举报邮箱:jubao@vip.sina.com
Copyright © 1996-2020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