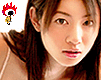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 纪录:太行山的最后一名电影放映员老杨(组图)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05 10:08 DEEP-中国科学探险 |
|
撰文/摄影 曾年
 [1] [2] [3] [4] [5] [6] [7] [8] [9] 【正文】 去年初的一天,我在旅行途中接到了一个来自巴黎的电话,是法国《V.S.D.》杂志(V.S.D.就是法语周五、周六和周日的缩写)的编辑看到我于1997年底拍摄的一个的故事,问我故事中主人翁、电影放映员杨元会的现状。我立刻挂通了一位朋友的电话,是他引荐我认识的杨元会先生。当年杨先生所在的北庄村尚未通电话,连手机信号也没有。今天也许通了电话,可又有谁会知道杨元会的号码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自2002年起山西省壶关县的电影发行已经停止,也就是说杨元会已经不能再干这一行了。挂断电话我想:1997年底的一幕应该是当地农村电影的最后一幕,杨先生自己如果还保留了一两部电影拷贝的话,他那架上海产的放映机应该还是能转动的,他就真的如同那天调侃中自己所说的:“如果真的没有人看电影了,放给老天爷看好了。” 1997年底的一天,我根据《山西日报》上的一条消息,来到太行山区的壶关县,冒着严寒寻找仅存的电影放映员。整个县城被取暖烧煤的气味所笼罩,电影发行站里味道更甚。这里似乎自1970年代之后,时间便凝固下来,尚未闻到改革大潮的气息。那时全县还有110个登记注册的电影放映员,由县发行总站去长治市电影发行公司租来电影拷贝胶片,再向5个发行分站发送下去。但是县城中唯一一家电影院,因无人看电影已经关门,凄凉地蜷缩在寒风扫过的街道边。 记得有一年,一部《天堂电影院》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讲的是意大利小城中一座电影院的兴衰,男主角自幼在电影院的伴随下成长,待其中年之后回到家乡,面对那座已经消沉颓败的电影院思绪连翩,一幕幕当年的盛景浮现眼前。当年的县电影院几乎就是小城的中心,上映的每一部影片也就是这里人们兴趣的中心。看这部电影时,许多观众与我一样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经历,感慨万千。 而在壶关县败落的电影院前,我童年时看电影的情形也依然清晰如故。一般都是周末,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我左右拉着父母的手,一用力便可以如同荡秋千似的荡起来。银幕上的画面今天已经想不起什么,但平时不让吃的零食总算可以吃到了。多数时候回家路上已经睡着,由父亲背着。待到上了小学,由学校组织看电影,便是一项仪式性很强的活动了。先要在学校里排好队,队形队列一番。上得大马路,行人车辆也必须让行。进了影院便如同炸了锅,说话必须高声喊叫才能听见。就连电影放映之中,也难得安静多少。次日的话题便是电影的情节,而且课堂中也会穿插着对于影片的提问或讨论。片中的英雄自然是我们的榜样,而笑料当然来自反面丑角。 言归正传,我们的探寻并未旗开得胜,找到的第一个电影放映员说由于没有老乡来请,已经有些日子不曾放电影了。我们就继续往大山里走,终于在北庄村的一个窑洞里找到了杨元会先生,他说当晚就有电影要放,而且是在本村。我们喜出望外,又请杨先生开了另一孔窑洞,我便可以留宿当地了,我的朋友则跟车返回县城。 北庄村坐落在一个山沟里,村里人一半住房屋,一半住窑洞,对面的山上还有一座城堡。老乡讲城堡是用来躲土匪的,最后一次使用是在抗战时期躲避日本兵。村后面的一片山梁已经退耕还林,“农业学大寨”时期建设的一点水利设施也已荒废。杨元会家种着4亩旱地,他的庭院里养着不少家畜,由他太太向平花操持。 午饭时间到了,8岁和12岁的两个女儿也放学回到家。北方农村的饮食非常简单,就着一点咸菜吃大馒头,除了节庆喜日,肉是见不着的。饭后,杨元会将他的电影放映机请出来,架在窑洞中进行清理。这两孔窑洞是1979年他们结婚时箍的。因为山西产煤,冬季取暖不是问题,他们全家人睡的那孔窑洞之中,也没有看见传统的土炕。倒是为我开的那一间里盘了土炕,和他们做饭的炉灶相连,做饭时土炕也就被烧热了。这架上海产的电影放映机是16毫米的,整个农村电影放映体系使用的应该都是这个规格。10年前杨元会购得时花了2000元,曾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北庄村有300余户、1500人,只有杨元会的一架电影放映机。 下午,杨元会在村中一块空场子旁的房屋上吊起银幕,全部放映家当用一副挑子就能挑走。今天是东家的小孩过周岁,这是乡亲的规矩,有红白喜事、生男孩、过周岁皆要请电影,钱当然是东家出。今天上映的是国产警匪武打片《摇滚杀手》。东家是没办法点电影看的,放映员取到什么片子,乡亲们就看什么片子。如果片子实在不好,杨元会还是会放,因为“反正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真的没有人看,放给老天爷看好了”。 不过,当晚倒没有悲惨到如此境地。天黑之后,老人、小孩陆陆续续搬着凳子前来,当然已经见不到我小时候经历的那种露天电影场面了。那时不仅是万人空巷,而且数里之遥的乡亲,也扛着板凳、打着手电前来助兴。而这场魔术的中心就是电影放映员和他那架神秘的放映机。如今的人们对电影放映员已经不那么崇拜,而老乡们对影片的内容好像也不太挑剔,但与从前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相比,似乎又有所不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倒是先出台了一批所谓“毒草”影片,跟随批判之际我倒也看过几部。这也就成了十10年文革之中的美好回忆了。因为后来的腥风血雨中,电影、戏曲皆由国家最高领导来审批,老百姓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几部有限的影片。但仅是这几部有限的电影,也成了这段年月中难得的一点点轻松。我想,在今天如果说到《地道战》、《地雷战》也是可以找到应和的。再往后一点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更是被人们不厌其烦地看上10遍20遍,每个人都会背出一通电影中的台词,或者是列宁,或者是瓦西里、托洛茨基。但是更主要的兴趣,还是影片里的亲吻场面,和其中一段芭蕾舞《天鹅湖》,加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每天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搞得麻木不仁之际,真如同一股暑天清泉。 文革后期也曾公映过一批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对朝鲜的《卖花姑娘》大家先是持怀疑的态度,怎么还有姑娘?还要卖花?不反帝反修啦?后来还真是事实了,因为该片故事缠绵,曾有影院中哭声四起之事。大都是因为当年文革之惨烈,观众以银幕人物自比,在黑暗中涕泪奔流一番,也可以痛快几分钟。最后有“朝鲜电影哭哭闹闹、越南电影真枪真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之说。因为当时的越战正打得火热,所拍影片也无不枪林弹雨;而阿尔巴尼亚到底是欧洲国家,稍微地人情味了一点,我们身处文革中的同胞也难以招架。最后几部罗马尼亚电影,放映时限制场次,一个单位的人必须由抽签来定谁能前往。当时我没有气力去与同事们争这一殊荣,而自己有位好友是影院的广告员,请其为我在黑暗之中寻一个座位还是可以启齿的。 终于,电影可以开禁了,那是在1970年代末期。有段时间大小影院剧场皆长时间不停轴地放,似乎要把所有库房之中可以找到的旧片子都拿将出来放一遍。记忆中我曾在这期间看过几部不朽之作,如《罗马——不设防的城市》、《马门教授》等。大家都有一种心境,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就是要补回文革中失掉的机会,人们的耳目已经饥渴的太久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江苏洪泽湖中,经历过一次为渔民放映电影。一支流动电影放映船在湖里支上架子,方圆数里的渔民皆驾船前来观看。当年鲁迅描写的社戏与之相距不远,只是没有“悔不该,酒后斩了郑贤弟……”之唱段,而改换了一部当时的国产警匪片而已。同样是我看不出区别的警匪片,在那天晚上的太行山村,并未赢得几年前洪泽湖中的热烈场面,不知算不算好景不长。 太行山区刚下过一场大雪,第二天我就与杨元会一同蹬自行车去另一个村换电影拷贝。拷贝胶片的租金最低一天15元,最高的可以到100元一天,在当地历史上租片价最高的是《开国大典》。说实在的,每天让老百姓看大同小异的功夫片、警匪片,确实也是乏味。不知怎样才能改变一下如今的窘境。 回答完《V.S.D.?》编辑的提问之后,我依旧继续行程。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坐车还是乘船,或者进饭馆吃饭,甚至连飞机上……总是有一架VCD(DVD)机器在不停地播放着武打片或者警匪片。刀枪并举,血肉横飞,一片打杀,有时候张艺谋的《英雄》也在其中。为了减少不停灌进的打杀声,我只好找两块棉花将耳朵堵起来。 有人说,人类最早先的时代叫作英雄时代,东方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西方有宙斯诸神和奥德修斯……之后经过青铜时代,最后才是黑铁时代。到了黑铁时代就是打打杀杀了。电影的历史是否也是如此?最早有郑君里、周璇、英格丽·褒曼,最后就只剩下李连杰和秦始皇了? (编辑:独孤)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