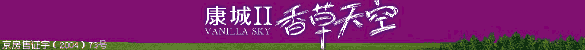| 东非高原守望者--埃塞俄比亚(9)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10/27 15:04 DEEP-中国科学探险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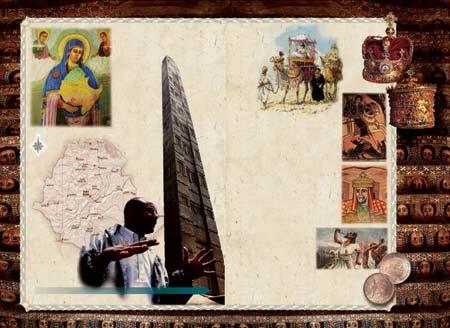 夜蒙蒙细雨之后,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主楼门前,社会学系本科生埃斯亚斯·伯哈努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来早了。今天也许是他和同班同学最后的一次全体聚会,因为一个小时后拍过毕业照大家就要各奔前程了,而他自己则选择留在学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当伯哈努和同学们对着镜头留下灿烂笑容的时候,也许不会想起脚下站的这个地方曾经是6位同龄人被枪决之处。时隔67年,两代年轻人在同一地点接受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安排。这6个人被处死的理由是他们用炸弹炸伤了素有“屠夫”之称的意大利总督格拉亚安尼(Marshal Adolfo Graziani)。此前,已经有3万同胞被报复性地屠杀,其中包括与侵略者拒不合作的主教彼得罗斯。他们的纪念碑就树立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门前环岛中央,俯视熙熙攘攘的街市和车流。大屠杀之后更多的年轻人愤然离开首都,来到乡村参加了当地的抗意游击队,5年之后,在美英盟军的帮助下,他们将意大利军队赶出了埃塞阿比亚。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昂提纳夫对我说:“抵抗外族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保卫东正教信仰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三大理想。”如果说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传统在伊斯兰文明包围下得以保全至今,很重要的因素是易守难攻的高原山区地形和对东正教信仰的坚定,那么能够阻止野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建立一个“意大利的东非”的,就是“埃塞俄比亚人强烈的爱国主义”。出生在亚的斯亚贝巴、获得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阿贝贝·扎格伊教授对我说。 亚格拉姆·塔迪斯是亚迪斯亚贝巴大学商学院二年级的本科生,当我们拜访他家的时候,他正准备到学校去复习功课。他告诉我:“在非洲,身为埃塞俄比亚人觉得十分骄傲,只有我们始终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塔迪斯有信心拿到学位,他选择商业管理这个热门专业也是为了有朝一日得到高薪职位。然而当我问他毕业后的打算,他显得有些茫然了。 坐在一旁的母亲发愁的可不是国家大事,而是儿子下一个学年的学费,因为塔迪斯没有伯哈努幸运,政府决定高校从下半年开始征收学费,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标准是每学年500比尔,相当于人民币470元。按照最理想的情况,塔迪斯要想攒够儿子的学费,至少得用半年的时间。 几天之后我们在青尼罗河瀑布附近的一条山路上碰到了另外一位母亲。她站在距离我们10多米外的一颗大树下,手打凉棚正焦急地呼唤着一双儿女。她的女儿肩背水罐,分明不过十一二岁,拉着比她小几岁的弟弟准备回家。陶制的大水壶压在这个小女孩稚嫩的背上,两只光光的小脚熟练地躲过地上尖利的碎石子。“村子里像她这样的孩子每天都要去两公里外的尼罗河背水好几趟”,向导勒加司继续说,“就在瀑布上游不到1公里处,政府的大坝截断了几乎所有的水流。这样做是为了利用有限的资源发电,可附近村民获取生活用水却变得辛苦。”我知道,这个国家虽然土地肥沃,但每年几个月的雨季之后可能滴雨不下,基本上每隔十年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大旱,随之而来的就是令埃塞俄比亚人深受其苦的饥荒。仅2000年那次饥荒,就有800万人受到影响,政府紧急抗灾,国际社会也送来人道主义援助。 “比起天灾,人祸更加可怕”,勒加司和我站在巴哈达(Bahir Dar)郊外的山岗上俯视青尼罗河时说。就在我来到这里之前3个月,巴哈达以西30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屠杀,上千人因此送命。我猜,勒加司一定是把部落仇杀归咎于稍显脆弱的“民主”制度了。 对此,昂提纳夫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开车带着我从首都出发沿着东非大裂谷一路向南疾驰500多公里来到内卡沙国家公园。这里生活着南部人口最多的民族——奥罗摩人(Oromo)。烈日严严的中午,昂提纳夫把车停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中间。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理解了他的用意。一支由奥罗摩族妇女组成的赶集队伍浩浩荡荡从汽车边走过,个个汗流浃背,弯腰光脚,行进在火成岩碎石子上。她们顾不得休息,因为家里的男人和孩子还等着她们背上的盐和衣服等生活用品。她们的家距离集市30公里,一周赶集一次,来回需要四天的时间。“这就是生活!离我们几十公里之外的部落,人们每天衣不遮体,食步果腹,‘民主’对他们而言首先是吃饱穿暖!”昂提纳夫认为在真正民主的框架里,给予地方一定自主权才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调动积极性。然而关键是如何实现,哪条途径是最现实可行的?“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的和平和统一来之不易,我并不希望看到第二个‘厄立特里亚’出现。” 从1998开始,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持续两年多的血腥战争至少夺去了数万名士兵的生命,另有数十万人沦为难民,光武器一项,两国就至少花费了10亿美元。 临别之际,昂提纳夫送给我一件木雕,那是只瓦利亚野山羊(Walia Ibex)。据说这种动物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多山而干旱的高原、峡谷,用头上的长角抵御狼群的围追堵截,向着祖先曾经徜徉的草原行进,寒暑往来从不间断。这使我想起拉里贝拉一所教堂里面,圈缩在白袍中的饥饿妇女露出一双炯亮又不安的眼神。她早已疲惫不堪,但却又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日子是苦难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要继续过下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责编:思琴)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DEEP中国科学探险第10期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