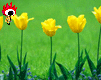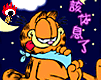| 老汉布里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9/14 21:36 DEEP-中国科学探险 |
|
作者:曾年 “见到过毛主席没有?” 我知道那次拍“长征”是1986年的事儿,故意开个玩笑。 “见到过,那是在1965年。” “你进去过人民大会堂没有?” 他反问我,然后说: “……我见到过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无论去老汉那里正式做客还是略略小坐一会儿,总是令人愉快,不仅老汉的言行为人师表,而且老汉如同一部摄影百科全书,有问必答。老汉的摄影生涯开始于50年代初,其人几乎就是世界50多年来的一个见证。 笔者曾以布里老汉为对象,写过一篇《目击世界40年》,据说曾引得《我们这一代》的作者、摄影家萧全先生涕泪奔流,还将笔者文中的一段引入他的这本书中。让萧全先生如此地动感情,真是不好意思。 写这篇文章的日期是1992年。转眼12年过去了,当时老汉还是风尘仆仆,跨着相机,奔波于天南海北;这次去老汉刚搬的新家,忙乱之中看见一堆过了期的胶卷,他顺手拿了几卷让我回去试试,看还好用不。 老汉明显老了,前几天还摔了一跤,摔得够狠的,幸好没伤着筋骨。跟老汉聊起摄影,他却说这些年来自己主要在编书和做展览,说也是“照片另外的一次生命”。这句话着实让我好想了一会儿。的确,老汉的名字越来越响亮,今年初巴黎一间市政府的摄影博物馆展出了老汉的摄影生涯回顾展,据展方说创下了建馆以来的最高票房收入,这个展览正在世界各地巡回着。一部关于老汉生平的纪录片也正在欧美几家电视台播映。用一个中国词汇来形容老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那就是德高望重。 奈,“从小好出风头”,同学们都这样说。 一个周末,小何奈参加了野营登山,接近山顶的时候,用刀割断了保险绳索,第一个登上了顶峰。 小何奈心里明白,至于出风头与否,那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山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小何奈失望了,因为瑞士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的后面还是山。一年一年过去了,小何奈成了小伙子,该去参军了。按照瑞士法律,男青年必须从军。 列兵布里申请当飞行员,驾驶战斗机,飞机飞得比山高,可以看见山后面的世界。所有的考试,所有的检查都通过了,没得说,要签字了,上面说,七年不准离开瑞士!小伙子布里不干了,他急着要带照相机去看整个世界。 几个月之后,何奈选中了巴黎去度假,理由是大画家毕加索当时住在巴黎,何奈找到了大奥古斯丹街。也就是在这里,毕加索完成了他控诉法西斯暴行的惊世之作——《基尼卡尔》。 何奈按响门铃。毕加索的秘书问:“你有约在先吗?如果没有的话,对不起,毕加索先生很忙。”说着就关上了大门。 就这样整整一个星期,何奈每天一次地来到大奥古斯丹街,按响毕加索的门铃,毕加索的秘书每天一次地重复一遍第一天已经说过的话。 青年何奈心想,这趟巴黎之行总不能就这样结束了吧!于是,他踏过了塞纳河,来到了位于北岸巴黎第八区的弗布圣朵诺埃街的玛格南图片社。 在玛格南图片社的办公室,何奈拿出了他认为好的照片:漂亮的太阳投影,抽象的墙壁……还有,还有…… “你还有别的吗?这些漂亮的照片对玛格南来说是零,对不起。”一位西班牙籍的女士说道。 “噢,噢,还有三个胶卷的打样,是关于弱智儿童的。”青年何奈说着,取出了三张打样。 那个西班牙女士开始兴奋起来,像是疯了一样,拿了一枝红铅笔在胶卷打样上画了许多圈儿。 “这张给我洗15张照片来,尺寸是……你用笔记一下……这张给我洗10张来,尺寸……” 何奈搭便车回到了苏黎世。 两个月后的一天,何奈接到一个邮包,上面盖着玛格南图片社的戳子,打开一看是一本大名鼎鼎的《生活》杂志!翻开几页,看见了自己的照片,何奈兴奋地跳了起来,直到天花板! 几天之后,理所当然的是一张玛格南汇来的支票。何奈·布里马上回到了法国,做了他的第二个图片专题。 真正的万里“长征”刚刚开始。 天,何奈正在捷克的斯格达工厂为纽约的《时代》杂志采访,忽然接到了从巴黎玛格南图片社来的长途电话,大卫·西摩用他那浓重的波兰口音说道:“何奈,你必须马上回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了!用你的瑞士护照可能被许可进入埃及。” 真的,何奈和另一个记者进入了正在发生事变的埃及,工作是相当艰苦的,到底是一张西方人的面孔,处处受到检查。何奈终于还是拍到了最后一艘油轮驶出苏伊士运河的照片。回到开罗,何奈·布里试着用种种办法把胶卷寄出去,到底请到一位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偷偷带走了胶卷。 一个星期之后,何奈·布里回到巴黎,大卫·西摩大发脾气:“你是怎么搞的?我们错过了发表的机会!你不能在玛格南工作了!”原来,何奈的胶卷在机场办公室的抽屉里睡了几天的觉。 对何奈本人和玛格南社来说这都是一个损失,下一次,大卫·西摩亲自约了一位《巴黎竞赛》杂志的记者又去了埃及,但是最终没有能回来,大卫中了枪,长眠在金字塔下的苏伊士运河港口。 罗伯特·卡帕在越南踩上了地雷;维尔奈·比邵夫留在了南美;现在轮到大卫·西摩了。个头儿高高的卡迪埃·布勒松从亚洲回到了巴黎的玛格南,似乎这个坐落在巴黎的小小的摄影师合作社里仅有他才是真正的法国人。 于中东的冲突不断加剧,何奈一次又一次地以他的中立国瑞士护照进进出出,目睹着事态的发展。 何奈在一点一点地汲取经验。 不是每次的工作都会有结果的,经常是冒了险,花了钱,浪费了精力,而没有任何收获,这意味着将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干这一行就是这样,甚至就连选择拍摄主题也是在冒着一种风险,像是在赌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罗伯特·卡帕生前常玩儿赛马彩票。那时刚刚诞生的玛格南社往往是靠着赛马场上赢来的钱维持着的。大概所有的人都有这种体验,每次冒险之前都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是一遇到机会,老毛病就又犯了,因为冒险的快感是难以抵御的。 1957年底的一天,何奈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圣·赛马斯迪安市的一条街道上等着拍摄佛朗哥及其车队的通过。忽然,两个军警上来把何奈打翻在地,一通好揍。已经这样,照片是别想再拍了,揍一顿算是客气的。何奈的鼻子流着血,回到了自己那辆破旧的大众牌汽车里,休息一下,准备开路了,无意之中翻开当天的报纸,发现一条小消息:大画家毕加索明天去法国南部的尼姆市观看斗牛。 圣·赛巴斯迪安距尼姆有500公里,还要翻越比尔耐山脉,当时是没有高速公路的,何奈糊里糊涂地驾了一夜的车,天微明之际,才到了尼姆市。他看到一间很小的名叫“白马”的旅馆,里面传出美妙的音乐声,上前一打听,还有空房间可租,便将行李器材搬上了二楼。 “请把行李都放下,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服务员小姐对他说着,顺手打开一扇门。 音乐的声浪使得何奈清醒了一点,他看见的几乎是一个交响乐队,而乐队围绕着的那个人,就是巴布罗·毕加索,他正装模作样地指挥乐队。 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找寻了几年的大师,何奈马上用他的莱卡相机拍了起来!而且和毕加索握了手! 再一觉睡到上午十一点多钟,何奈恍恍惚惚地走下楼梯。一个年青人急急忙忙冲上来,拉上何奈就往回跑,大声喊着:“跟我来,跟我来!” 进了一个房间,何奈看见一幅达·芬奇油画《最后的晚餐》中的场面:长长的饭桌,白色的桌布,一副副的餐具……所不同的是,坐在中间的是毕加索,围坐着的人正整齐地用手拍着桌子,齐声喊着:“我们十三个!”、“我们十三个!”(基督耶稣的最后晚餐,是和十二个门徒一起共进的,所以是十三个人) 那个急急忙忙的青年人一进门便喊道:“爸爸,我找到了一个人,就是那个摄影师!” 毕加索说了一句:“请坐,开饭!” 原来,毕加索说过,如果整十三个的话,他就不吃饭。 何奈·布里的梦想成了现实,玛格南图片社的总部也离开了罗伯特·卡帕时代的巴黎八区旨布圣诺埃街,搬到了拉丁区的大奥古斯丹街,成了毕加索的邻居。我们的主角——何奈·布里,也于1959年在纽约成为玛格南图片社的正式成员。 “长征”仍在继续。 着的拉美革命、“越战”、中东的“六五战争”、人类登月、航天飞机、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世界……面临这世界上一个接着一个的热点,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何奈·布里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不回避新技术的运用,从大广角镜头到望远镜头,到彩色胶卷,到影视声像技术……他没有听从尊敬的导师卡迪埃·布勒松的劝告:永远的黑白胶卷,永远的标准镜头,永远的一瞬间,永远的…… 德语是何奈·布里的母语,另外他会说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明年他就72岁了,头发白了不少,明天他还要飞美洲为美国的《国家地理》拍一个专题。何奈来过中国7次,他希望再来几次,并希望在中国开一个自己的展览会,向中国人说几句心里的话,展示自己50年来所目击的一切和这个风云多变的大千世界。他一生后悔两件事情:一是没有学会俄语,一是没有学会汉语。如果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他仍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新闻专题摄影这一行。这个职业的人都不会发财,不会成为巨富,在付掉旅馆、胶卷、冲洗照片费、飞机票、电话电传费等等等等之后,剩下的只够往破旧的大众牌汽车里加一点汽油。但是,“因为我们是事件的参与者,我们目击了世界!”何奈·布里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所以他是“富有的”。 他还和年青的时候一样,在乘着波音飞机的回程中画着关于那个刚刚离开的国家的印象的水彩画。他还是和小的时候一样,喜欢登高,渴望看见大山后面的,更深更远的景象。 (编辑:思琴)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DEEP中国科学探险第09期 > 正文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