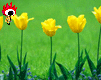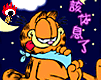| 当代长篇小说选登:英格力士(第一章)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9/13 15:13 当代 | |
|
作者:王刚 王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生于新疆石河子市。曾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及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 1987年在《当代》杂志发表小说《冰凉的阳光》,之后有小说《博格达童话》《红手 第一章 1 乌鲁木齐就是这样,经常是太阳和雪花朝你一起冲过来,而且是在春天的五月里,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口里人连田野和桃花看得都有些烦的时候。 阿吉泰站在讲台上,她没有说话,眼泪就先流了出来。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男孩儿都会心情沉重?因为阿吉泰要走了,而且她长得漂亮,她皮肤很白,她是二转子,对不起,二转子是乌鲁木齐话,我得翻译:那就是她妈妈是维族,她爸爸是汉族,或者相反,她爸爸是维族,她妈妈是汉族。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学俄语了,从今天开始就不学维语了。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尽管她是女老师,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 教室就像是河边的原野,我们是欢快的昆虫。阿吉泰转过身去,我看见了她的腰,还有腰下边的部分,它们在扭动,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然后,她用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毛主席语录。她勉强写完这几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她转过身来,用汉语说:我不想走,不想离开你们。男生噢的一声,开始像麻雀一样地飞来飞去,就好像那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天空。阿吉泰看着我们这样,她笑了,她的笑像谁呢?有谁的嘴唇能跟她比?李垃圾突然大声喊起来:毛主席万岁。 全班都笑了,这次也包括女生。然后,然后是大家和李垃圾一起喊:毛主席万万岁。阿吉泰等欢呼声停止之后,才说: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想让我留下? 教室静默下来,阿吉泰想错了,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更不要说维语,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English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过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 阿吉泰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我的脸上,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学英语。昨天我见了你们的英语老师,是一个男老师。他叫王亚军。男生立即噢的一声,表示不屑。 窗外的一切都像雪花一样游手好闲,我朝高处望去,天空蓝得让我想哭。面对那些说不出道理的色彩,百感交集的为什么总是我这样敏感的“儿娃子”?他长着巴子,在五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他已经有些变声,他对天空的迷恋程度远远超过他同班的女生,尽管她们身上的衣服连补丁都是有色彩的。儿娃子和巴子都是我们乌鲁木齐话,如果你们人和外国人硬要让我又一次翻译的话,我得慎重一些,然后说:就是长着鸡巴的男孩。 很静很静的,没有人再说话: 俄语走了,维语走了,英语就要来了。 2 博格达峰就在我的前方,那儿是乌鲁木齐河的发源地。在清冷的五月,我走在泥泞里,阳光灿烂,我手里提着饭盒显得亮晶晶。我是去给父亲送饭的,他早晨说中午就不回来了,他要尽快把那幅画画完。 剧场的对面搭起了一面墙。爸爸站在脚手架上,他刚画完了一个人的头像,现在正在画他的肩膀。在我们所有人都很瘦的时候,那个人却挺胖,他就是毛主席。 我走到跟前,说:爸爸,吃饭了。爸爸没有理我,他仍在聚精会神地画着。我说:爸爸吃饭。他没有回头,说:像吗? 我看了看,说:好像是少了一只耳朵。 父亲说:你懂什么,那叫透视规则。我说:就是少了一只耳朵。父亲有些生气了,他停止了画画,把眼镜正了正,从脚手架上往下爬,他的姿态灵活,像是西公园里的猴子,攀伏在钢管和木板之间。晃悠了几下之后,他跳了下来。我看他额头上都是汗,就说:画画很累,是吗?他说:那要看画什么了。我说:你看,是不是少了一只耳朵?爸爸说:以后要有可能你也要当建筑师,画画的基础。说着,他拿起了一块包谷饼,吃了一大口,可是他不小心却咬了自己的手指,疼得他看自己的手,没有破,只是咬出了牙印。他笑了,说:馋了。又有好多天,春节过后,就没有再吃过肉,想想吃过的猪蹄,已经是很早的事了。 我看着画像,听着爸爸嘴里的咀嚼声。他的牙齿在打磨着包谷饼,就像是工地上的搅拌机在来回翻动着石子和水泥沙浆。我的眼睛始终盯在了那一只耳朵上。 爸爸似乎感到了我的固执,就说:我告诉你什么叫透视规律。你看我,以这个角度站着,你是不是只能看到我半边脸,还有一只耳朵?还有鼻子和嘴的轮廓?我要是转一转呢,他说着,把最后一块饼放进了嘴里,就稍稍转了一下…… 我高兴地说:能看到那只耳朵了。 他明显不高兴了,说:能看到吗?看不见,你只是在看我的头和我的面部,如果你非要看到我的耳朵,那我得这样,他说着,又要转,可是,他却紧张起来。 从不远的楼里,走过来两个男人。他们一个戴眼镜,一个不戴。戴眼镜的是范主任,不戴的是一个很高个儿的男人。 爸爸显得有些紧张,说:你先走吧,回家去,对妈妈说,我今天画完得早,就早回家。我说:下午没课,我看你画画。爸爸说:走,回家。我却仍是不走。爸爸的眼神里显出了无奈,甚至于有某种恐惧。显然,我在这儿使他更加紧张。我看着爸爸的眼睛,有些犹豫了,如果他再要求我走,那我就听他的,可是他已经没有了时间。这时,那两个男人走到了跟前。其中那个没戴眼镜的高个儿看了看画,说:像,真像,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的就是这样。突然,他愣了一下,说:为什么只有左边耳朵,没有右边的?我有些得意,爸爸肯定错了,而且是我最先发现的,只是他还不肯承认。爸爸看着画像,对他说:范主任,申总指挥,这是透视规律,你想想……那人看着爸爸,说:什么规律?你赶快上去,把那只耳朵给我补上。父亲没有动,只是脸上堆满了笑,好像他十分喜悦。他说:补上以后,就不像了。那人走上前来,先是抓着爸爸的手,然后,他改了主意,他把爸爸的耳朵用手一捏,然后轻轻拉着。当他发现爸爸没有跟上自己的节奏,就使劲拉起来,并说:快,爬上去,给我把那只耳朵补上去。戴眼镜的范主任一直在笑,并说:让你补,你就补吧。父亲看着他们,犹豫着,他看着范主任似乎在求救。因为,父亲知道,范主任也是知识分子,他不但懂得透视规律,而且懂得更多。 我本来在跟那人一起笑,可是当看到他揪着爸爸的耳朵时,我不想笑了,我想对他们说,你放开他的耳朵,可是我不敢。我感到自己的耳朵也有点疼起来。 爸爸开始灵活地爬了上去。 我在下边看着他的头发在颤动,他的眼镜上泛出阳光。 他拿起了笔,给画面中的那个人的右边又加了一只耳朵后,我们都愣了: 他的整个脸都变了形,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脑袋和脸。 那个人说:你胡画,你把耳朵加得太大了。 爸爸又擦掉了那只耳朵,把它画得小了一些。毛主席的形象变得更加滑稽。然后,爸爸说:不能加。那个人说:你下来吧。范主任也说:快点。爸爸下来了,他跟那两个人一起看着画像。突然,范主任抬手给了爸爸一巴掌,把爸爸打得几乎摔倒。范主任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说完,他讨好地看看那个高个儿。高个儿的申总指挥说:你给我全部擦了,重新画。说完,他们要走。我冲上前去,拉着范主任的腿,说:你为什么打我爸爸?他笑了,说:你是小孩子,再大一点就要和他划清界限。我死死拽着他,不让他走。他对爸爸喊道:快快,把你儿子拉回去。爸爸对我吼:回来,放开叔叔。我还是不放。爸爸上前拉我的手。我仍然显得固执。当爸爸发现他狠狠拉我,我竟然不松手时,就朝我屁股上猛地踢了一脚。我吓得松开了手,感到爸爸真是用力,我感到很疼。 那两个人走了,戴眼镜的人一直在跟高个儿男人说着什么。 爸爸一直看着他们走远,才问我:疼吗? 我摇摇头。爸爸叹口气,说:下午开始重新画,画一个完全正面的像,那样两只耳朵就都有了。 我说:他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 爸爸说:我打不过他。 爸爸说着,看看我抽搐的脸,就轻轻拍拍我的头。 我看着爸爸刚才被揪的耳朵,说:那你为什么要打我? 爸爸笑了,说:傻儿子,我不打你打谁? 这句爸爸的笑话进入了我的回忆。现在人们经常爱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此刻我也重复一下吧: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那就是看着父亲挨打的时候。 3 晚上,我在床上睡不着。爸爸挨打后的笑容一直闪现在我的面前,像是风雨中晾在窗外的衣服,晃来晃去,使我像是睡在了摇篮里。然后,我听见了另外一间屋子里传来了爸爸的哭声。我感到恐怖,那声音就像是乌拉泊风口的抽泣,很有些绝望的味道。 我悄悄起身,到了爸爸妈妈的门口,轻轻推开一点缝,朝里看着。爸爸的确是在哭,他说:他今天真的打我了,我的左脸很疼。他们不懂,什么都不懂,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妈妈为摸着爸爸脸,说:是不是这儿疼?爸爸仍在可怜地哭着说:我真是没有想到,去年开批斗会的时候,也没有批我,也没有打我,今天,他们是为什么?妈妈说:可能今天是他心情不好。爸爸像是一个充满依恋的病人一样,对妈妈说:我的白头发是不是又多了?妈妈看着微笑起来,说:来吧。 爸爸顺势把头伏在妈妈的腹前,低下去,让妈妈开始仔细地帮着他找白头发。妈妈找得很仔细,然后,一根根地拔下来。爸爸舒服地享受着,就像是一只不停哼哼的狗。每一根白头发下来,他都会轻轻地叫一声,然后把头挨着母亲更近些。母亲也很愉快,她叹口气,说:又是春天,又是一年过去了。爸爸说:这样的春天,不来也好。 母亲拔得有些累了,说:你好些了吗?爸爸说:你猜白文是死在谁的手里?妈妈一愣说:他是自杀的呀。爸爸说:不,他是被他妻子杀死的。妈妈不解地看着他。爸爸接着说:如果他妻子像你一样,那他不会去死的。自杀的男人都是被他们的妻子杀死的。妈妈说:昨天做梦还梦见了他送我们的那张唱片。爸爸说:我突然想听音乐。妈妈说:不行,没把咱们赶出这套房子,没让咱们去铁门关,去焉蓟就不错了,你还敢听这些东西。爸爸说:我只用很小的声音。妈妈说:那也不行。 爸爸不听妈妈的,他悄悄地从床底下拿出了留声机,又取出了那张唱片,说:格拉祖诺夫。真是让人羞愧难当,我今天非要写出格拉祖诺夫这个名字。就好像我跟爸爸一样,也是一个事儿妈,喜欢说说这些名字,实在是在这部小说里边,格拉祖诺夫和他的小提琴就是一个不谐和音,或者是一个扎进人手上的刺,始终萦绕在我的四周和我的身体里。 音乐声响起来,妈妈让爸爸把声音搞得更小些。我听着音乐,在缝中看着爸爸把妈妈抱起来,为她脱衣服。妈妈说:刘爱睡着了没有?爸爸不说话,把灯关上了。在黑暗中,妈妈的呻吟和小提琴的诉说混在了一起,就像是一条混合着沙子的河流,最后你什么都分不清了。 我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似乎妈妈叫床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格拉祖诺夫是我平生知道的第一个作曲家,他高贵的气质永远地跟爸爸妈妈可怜的做爱连在了一起。 就好像是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阴水融进了清水里。 (编辑:琪琪)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传奇玄秘 > 正文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